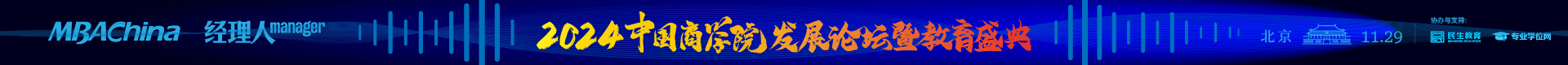余永定:不能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解释短期的经济下行,不能轻易放低GDP增速目标

题记:2021年1月19日,在两本新书《中国经济的前景》《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版上市之际,由中信出版集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信读书会共同主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暨中信读书会”线上举办。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共同就中国经济的未来与挑战进行对话。对话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赵秋运主持。由于余永定教授在对话中的内容相对独立而完整,且观点鲜明、紧贴经济形势,故单独摘出成文,以飨读者。

余永定教授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我简单谈几点。
首先,我们要对2021年的经济增速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以上,但如果去掉基数效应,实际增速可能低于5%,低于潜在增速。虽然我不相信任何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一定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通货收缩状态,PPI自2012年3月起连续54个月为负增长;CPI在过去10多年基本不超过2%,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往上涨,但最近又往回降了。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有时通货收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我们应该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相当高的令我们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它任何目标都难以做好。
顺便说一下,所谓“高质量的GDP”的提出用意是好的,这个表述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质量高或低属于微观经济学和中观经济学的问题,100亿元的GDP就是100亿元的GDP,不能说现在的GDP虽然比较少但是它的质量比原来的高。企业不顾质量盲目生产的问题是有的,但这是产业层面而不是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
我们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绝不意味着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我们只是强调,既然有可能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就应该努力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条件。反之,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
我们不妨看看2019年和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同比可能涉及到基数问题,我们简单看一下环比。
2019年各季度的年化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6.6%、4.9%、5.3%和6.6%,2021年前三季度的年化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0.8%、4.9%和0.8% (第四季度的数字还不知道)。由此可见,2019年和2021年之间的差距相当大。2021年的经济是在增速低于6%的情况下运行的,充分说明我们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增长问题。
如何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学界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存在许多方法论上的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解决,经济就无法增长;或者认为,如果追求经济增长,这些结构性问题就可能被忽视了。这是把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我想问,这个“结构性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在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导致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这一箩筐的宏观经济之外的问题,都用一个叫“结构性问题”的词装在了一起。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由于这样一些结构性因素存在,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这么低。
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2.2%,此后几乎每个季度都在降。如果说从12%降到10%是结构性因素导致,我可以接受,那么从10%降到9%、8%、7%、6%甚至5%,都说是因为结构性因素,我就认为不合适了。结构性因素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它是长期的影响因素,经济增速每个季度都在往下走,就不能用长期的慢变量来解释。
我对结构性因素有以下四点评论:
第一,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里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它对每年、每季度经济增速的影响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如前面列出的那些结构性因素,它们不仅数量庞大,且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但总的来讲,单个的结构性因素在较短时间内对GDP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第三,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讲它使得经济增速下降了,但我们还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就是抵消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吗?我们要看最后的结果,而不是说有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一定会低于6%或者5%。
第四,什么结构性因素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最直接的就是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另外一些结构性因素,则是通过非常长的因果链条影响到消费、投资等。如果你要想证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只能是6%,那你就得把每一个因果环节都给点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你得把ABC找出来;如果你根本找不到,然后你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我觉得这不能成立。
宏观经济讨论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假定那些结构性因素是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
比如消费为什么下去了?这跟人口老龄化可能有关系,但恐怕直接的原因并不是这个。2020年很多人主张像美国那样,通过政府给老百姓发补贴来促进消费。这肯定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消费者对经济增长和收入预期很悲观,即便你发了钱他也只会存起来。2021年好多人讲消费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增长,其实可能性不大,如果经济不能够真正增长起来,不能使大家的收入增加,不能改变大家的预期,消费增长就会很困难。
再比如人口老龄化对GDP的影响。人口因素确实与经济增长速度有某种相关关系,但不见得是因果关系。日本在60年前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现在低至1%左右。与此同时,日本人口也快速老龄化。这是一个长达60年的过程。老龄化肯定对日本的经济增速有很大影响,但将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摊到每一年来看,在每一年这种影响很小。
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值得重视,我想说的是,在分析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判断一下我们能不能使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一点。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一点,通货膨胀起来了,或者会产生金融危机了,那说明经济增长速度高不了,只能保持现有水平甚至还要再降低;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发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追求更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觉得,这是经济学界的方法论出了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老想着预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然后根据预测的结果来决定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把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算准了。中国更是如此,很多时候连基本的统计材料都没有。国家统计局在不断调整修改统计资料,美国也是,多年之后再对之前的主要经济指标做调整,可能调整一个或者两个百分点,但总共才三个百分点,这样的宏观经济预测到底有多大意义?
我们研究经济学有几十年了,碰到过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有人预测准了,但他可能一辈子就蒙准了那一次。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他大概就预测准过这么一次。还有位美国经济学家90年代初就预测美国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20年后终于发生了。有人说,“只要你坚持一个预测,永远说下去,你总要准一次”,但这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预测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认为它就是真理,就非得按照这个去做。
我特别欣赏过去的中国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搞不清楚前面是什么,大方向看准了,那就边走边看,这里面蕴含了相当多的道理。有些管经济的不懂经济学,但他们比懂经济学的管得好,这是事实。尽管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达到了年均10%。中国的GDP在刚改革开放时排名世界第18,小于荷兰,但到现在让美国都害怕了。中国的GDP在刚改革开放时不足日本的1/4,2010年赶上了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3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成功了就是好的。我感觉,当初决策者幸好没听信经济学家的一些非常scholarly(学术性的)的主意,否则实现不了10%这样的成绩。世界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经济做了很多预测报告,但许多都不准甚至和实际情况南辕北辙,那里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做了大量的调查。为什么会这样?我主要想强调的是,人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一种非常谦卑的心态去尝试,敢于尝试才是最好的。只要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失控,没有非常明显的金融危机风险,就应该争取让GDP保持更高一点的增长速度。
每年都有人在说中国面临危机。2012年我们去纽约交流,当时美国那边就说中国要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先是说房地产市场要崩溃,然后又说温州地下金融要把中国整个金融业拖垮。我当时说,虽然这些问题存在,但是它们根本不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当时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整个中国经济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们不能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它们也不会造成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种危机。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社会科学院,当时就在讲中国危机、通货膨胀,说笼中老虎会出来,但等了50年我头发都白了,这些危机还没等出来。如果那时候小心翼翼不让经济增长了,那中国肯定不会有今天。所以我觉得,经济学还不是一门十分严谨、十分确定的科学,尤其是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艺术性。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要用试错的方法,追求一个比较高的经济目标,而且我们有潜力和能力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以上。
2022年大家认为是5.5%,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毕竟还在受疫情冲击。我们应该有个目标,我不赞成不制定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引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要有个目标,这样大家才会围绕这个目标去制定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在制定每项政策时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说出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明确提出一个目标,大家再根据这个目标来协调行动呢?同时,这个目标定得也不要太低,我们用试错的心态去尝试,确实不行后再退回来也不晚,避免出现所谓的“经济磁滞效应”。一个人老失业,再就业就可能不适应,而一个团队因经济情况不好解散了,再组织时可能就没人气了,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所以我们应该就经济增长目标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的主流研究人员和北大的主流研究人员的想法非常接近。我们需要多交流,大家也要把想法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实现百年目标做出一点微薄但积极的贡献。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MBAChina立场。采编部邮箱:news@mbachina.com,欢迎交流与合作。
备考交流
最新动态
推荐项目
活动日历
- 01月
- 02月
- 03月
- 04月
- 05月
- 06月
- 07月
- 08月
- 0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11/03 上海线下活动 | 港中大MBA课程2025级招生宣讲暨校友分享会
- 11/03 上海站 | 港中大MBA宣讲会暨校友分享会
- 11/03 学长学姐校区见面会 | 香港大学在职MBA(大湾区模式) 十一月线下咨询会报名
- 11/03 下週日見!2025年入學交大安泰MBA第一場港澳台申請者沙龍重磅來襲!
- 11/06 讲座报名 | 房地产市场的破局与重构
- 11/12 统考倒计时45天 | 清华科技创新MBA学姐备考分享&答疑等你来!
- 11/13 线上活动|备考经验高密度输出,招生动态前瞻解析,11月13日交大安泰MBA考情解析+笔试技巧分享会开启报名!
- 11/14 公开课抢位|人工智能、数据和人才@北京
- 11/14 申请冲刺 | 港中大(深圳)MBM2025级第四批次招生启动!
- 11/14 活动日程 | 11月14日港中大(深圳)MBM2025级招生说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