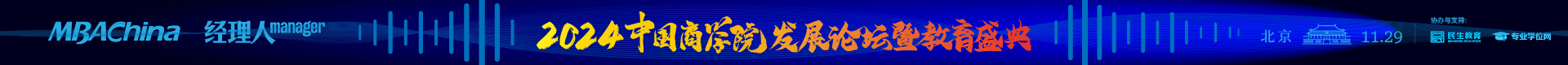姜锋:我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的40年不解之缘

2018-12-26 17:26 浏览量: 3702
★本文刊登于《外国语》2018年第6期第63-71页★回想起来,与外语教育结缘多半是偶然,偶然中的必然是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给新中国的外语教育又一个春天,对我而言,由此学外语则改变了我的人生。40多年来,我从学习外语到使用外语,从参与外语教育规划到教授外语,从用外语做工作语言直到今天在外国语大学工作、再次直接与外语教育改革如此地紧密联系在一起。40年的直接体会是:首先,外语教育是国家政治大事,40年来外语教育兴旺发达与新中国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使学习外语不仅仅是个人掌握外语技能,也是国家人才和智力的一部分,受到举国重视,体现在人才和教育等各项政策中。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就高度关注,由他关心的国家派出留学生计划中,外语人才的培养占据显著地位,1979年国家计划公派出留学生3000人,按学科分布,理工科占70%,社科类占15%,语言类占7%,科技与管理类占4%,其他占4%,语言类留学生的比重大到可以单列。其次,外语教育是教育制度中的“特区”,比如早先考外语专业,数学分数不计入高考总成绩,虽然这在全面教育理念中属于偏科,不利于人才全面智力成长,但能够体会到当时国家急需外语人才,免计数学成绩,为的是让学生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外语,“快*才”。再有,外语教育管理体系层级高、机构体系化程度高。教育部高教一司专设外语处,负责综合规划和推进全国高等外语教育事业,中小学外语教育也有专人负责。80年代初曾有过关于成立外语司的讨论,足见当时对外语教育的重视。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大中小学的外语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发展,国家加强了英语等以外“非通用语种”的教育。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学科体系设置方面,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独立单设一科,这在国际流行学科分类中是独特的,体现了外语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学科划分有明显的局限。近40年来,我的学习、成长和职业与外语教育密不可分,以下就从大学阶段的外语学习开始谈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其中透着我对外语教育发展变化的粗浅思考,与读者分享。大学:外语作为专业的学习“对德语不感兴趣,是对德国的事感兴趣”1980年,我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习德语,是自己的选择,可是真学起来却高兴不了。和中学比,环境变化太大,第一课上有的同学已经可以用德语打招呼了,自己却是地地道道的“零起点”,觉得距离很大,随后是一个多月的语音训练,天天是德语,没想到大学里的学习是这么枯燥无味,感觉不到生活现实和德语有什么关联,认定自己不是对德语感兴趣,是对德国的事感兴趣,在德语上不愿多花精力,“自甘落后”,怀疑学德语的选择是否正确。与德语课不同的是,法语系那时几乎每周都放电影,这强烈地吸引着我,虽然看不懂,但看得起劲,城市的景象,海边的男女人物、大楼、汽车、公路,一幕幕的事物让我觉得神奇:有这样的世界吗?对法国和法语的关注从那个时候扎下了根,虽然至今我的法语水平还不到“半瓶子醋”,但心中念念不忘。另外,让我着迷的是图书馆。那时的上外在给学生供给图书方面已经很先进,对学生部分开放图书,学生可以自由到阅览室去阅读,但抢到座位不容易。没有座位就只好站着看书,站得时间长了累了,就要走动,在书架之间边走边随手翻阅好奇的书,主要是英语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那时这样读的,还有英文版卡夫卡的《变形记》等。德文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德国人给高中生编写的读本,是各类名著的选段,包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节选,现在还记得选文很短,很刚劲,开头就是“Seht, ich lehre euch den Übermensch!”,为了理解,也是出于好奇,找来一本中文介绍尼采的书对比阅读,看到中文书把这段话译成了“看哪,我教你们超人”,觉得不够劲,应该是“听着!我教你们超人!”后来和班上同学交流,一位同学主张翻译成“呔!我教尔等超人!”,我暗自佩服这个“呔”字,这才叫霸气,有超人的样。还有一本德文Kleine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世界哲学简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对每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的学说介绍得言简意赅,在其中我第一次读到外国人介绍孔子的文字,这对来自于孔子家乡的我深感亲切,借助文本回到了家乡。与此对照读的一本是北京大学编写组文革期间出的《欧洲哲学简史》,可能也是出于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因,文字非常简练易懂,读之不累,即便是黑格尔和康德也被描述得很清晰,读时很快把握大意,对那时更多热衷于功利阅读的我是非常合适的。看来,图书馆里没有座位也有好处,就是得不断走动,不断换着书翻阅,正合“涉猎”的意思了。那个时代,不少书是为工农兵大众写的,文字简单,叙事扼要,容易阅读,现在,这样的书大概没人写了,也很少能读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里同学们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浓厚。大家默认的规则是,不谈点哲学就显不出水平,西方当代哲学的书十分抢手。除了食堂大家不得不去那里吃饭外,要数校园里那间很小的书店最能吸引学生,在先睹为快地翻阅新书、预订新书、期待订的书早日到货之间度过时间,生活很新鲜,很有期待。新书来了读不读是一回事,但总要拥有,这本身就是谈话的资本,底线是要能说得出一两个基本流派,几个名字和几句名言,不然,就很难让人感受到你有品位了。德语系的男生们还因着德语有些骄傲,甚至目空一切,对其他系的人谈尼采不屑,认为不懂德语,怎能明白德国哲学的奥妙,如何懂得Übermensch(超人), Macht(权力), Wille zur Macht(权力意志)的全部意义!现在想来,那时少年气盛,但另一方面看,德语专业同学们的专业认同度还是高的。因为把力气花在了德语以外了,我二年级上考试德语专业竟然没有及格,这给我敲响了警钟,意识到“对德语不感兴趣”是错了,要想毕业,想回家在父母面前有个像样的交代,就得认真对待德语,不能再自感落后了。努力很快见成效,德语上起码不再是末流,大致进入了方队的前三分之一。“美的事物也是或可能是危险的。”进入三年级后,学业开始变得有意思有深度了,不再全是单纯处理语言现象。张振环老师的精读课上来就讲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节选,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之战以后凯旋回家乘船遇到水妖的那段。奥德修斯让随从们塞上耳朵,并把自己捆在桅杆上,不让大家沉溺于歌声,避免船毁人亡。从语言角度处理完文本后,张老师让大家思考,奥德修斯为何让大家塞耳朵,为何把他自己绑在桅杆上,说明什么道理?讨论最终集中在一个辩证的结论上:歌声美妙,但可夺人性命,美的事物是或可能是危险的。这样的认识对80年代初的青年人来说是很震撼的,我至今印象深刻。张老师在课上有许多课外内容,诸如俄狄浦斯的故事、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都与当时流行的西方哲学热潮相对应,关乎我们学生们关心的问题。第一次听到男孩子都有恋母情结时,那是何等的震撼!由此而去读朱光潜先生的“变态心理学”,得知至今被人们普遍认为变态的心理,其实是正常和原本的心理,而被认为是正常心理现象的却深藏着不正常的动机,有着 Ich、Ego和Libido的关联。既然读到了朱光潜先生,那肯定离不开《谈美书简》和《美学》,由此扩展开来,近乎着迷一样地涉猎钱钟书、宗美华、李泽厚、蒋孔阳、朱狄等大家们的美学作品,惊奇地发现他们很多著作都有深受德国的影响,钱先生的《管锥编》里甚至有很多德文注释,这些让我深感亲切。读那些文本,是大学生活的难忘的内容,是深刻的那一部分,以往对人和生活的观念在一个个被动摇更新,世界变得宽广起来,丰富起来,而且,你觉得世界上的谜底你是能解的,这是青春时代的乐观精神,大学是激活这一精神的地方,对很多年轻人可能是唯一的地方。大学的课堂是直接的,对人的影响又是间接的,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加工消化。张老师引导我进入了思想的世界。印象中,德语系办公室主任木春老师开设的心理学选修课也很“时髦”。在介绍心理学基本概念的同时,他还介绍过“爱情心理学”,这自然也离不开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两位老师的课相映成辉,一起回应了学生的生活现实,我很喜欢。读书是渴求知识,更是体验生活,是与自己内心深处的对话交流,是认识自己。“字典错了!”王志强老师的德国戏剧课也是至今难忘的。他那时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上课声音宏亮,激情满怀。刚来上课,他便和同学们发生了“争执”。是因为一个介词搭配,有同学造句说“Ich habe keine Lust daran ...”,王老师纠正说,不对,应该是 “Ich habe keine Lust dazu”,那位同学不服气说:“字典里就是用的daran”,“字典错了!”王老师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场翻《简明德汉字典》“对质”,里面白纸黑字的确是“daran”,“这个字典错了,要查原版字典”,王老师说。原版字典里的确是“dazu”,也看到有不同用法。这次小小的辩论让我感悟到,被认为标准或是真理的字典也会出错,这动摇了我的权威观念:不要轻信权威。上王老师的课,面对更多挑战:上课没有课本,而是根据进度发给复印的文本选段。老师上课没课本,这本身就很与众不同,放到现在就是不合规了吧!而且,他给的德文文本很难,从亚里斯多德《诗学》的悲剧篇开始,寥寥几页纸足足读几天,从古希腊的历史背景,到悲喜剧的不同发展与特点,做了简单的知识铺垫,然后才进入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悲剧的要素是对情节的模仿,而不是人物,人物要服务于情节;情节制胜的关键是在观众中引起怜悯(eleos,Mitleid)和恐惧(phobos,Furcht),同情剧中人物的遭遇,害怕自己遭受剧中人同样的命运,在怜悯和恐惧中达到净化(catharsis,Reinigung),悲剧是引人向善的。至此,明白了悲剧和喜剧的差别,甚至对悲剧怀有了崇高的敬意,对喜剧却不以为然,觉得是肤浅的。“记不清了”文本阅读紧接着就到了莱辛的《拉奥孔》。现在想来,王老师这样的安排独具匠心,因为莱辛是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权威的解读者和发展者,也是创作市民悲剧的实践者,是通过文学推动社会革命的先锋。可以说,莱辛是革命作家和理论家。他的《拉奥孔》当然不容易读,但他托物讽世的寓言故事却是“短小精悍”,语言上易懂,算是阅读他系统理论著作的有效辅助,对学习德语更加便当。在图书馆里快餐式地读了几段莱辛寓言故事,算是先初步了解这是何许人。寓言《猴子和狐狸》(Der Affe und der Fuchs)只有三句话,但鲜明痛快地表明了莱辛的主张:德国作家们不能跟在别人(主要指法国的古典主义)身后模仿,要独立自主。《拉奥孔》便是对此展开的理论阐述。围绕《拉奥孔》的阅读和思考,我明白了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特点是题材在空间上的并列(Nebeneinander),文学的特点则是题材在时间上的先后持续(Aufeinander, Nacheinander),因此诗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成为画,这对我在中学语文课上学得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观念是不小的冲击!这也是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学种类之间的差别,意识到,这样的差别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在当年那个时代具有反抗的力量,是一场斗争。读莱辛的《拉奥孔》还引出了温克尔曼,因为莱辛在书中批评他“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stille Größe)的古典主义理论,反对文学创作中的“高大上”,要求文学人物要有鲜明的个性和表现这一个性的情节。在那本德国高中生读本里找到了温克尔曼的片段,大意是关于模仿的,讲希腊艺术高不可及,胜过罗马艺术,差别是希腊人模仿自然,罗马则专注描绘人物形象,差不多前者入于神,后者浮于形的意思,后人要尽力模仿希腊方可达到极美的境地。那一段文字不长,并未完全明白,只是懂了大意,这也是那时读书的功利习惯,浅尝辄止。有趣的是,仅仅读了一点温克尔曼,就对莱辛产生了警觉,没有被他牵着完全照着他的路走,他反对温克尔曼,但我感到后者“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是非常经典的审美理念,也是我至今不忘的一句名言。2014年夏,就是在大学毕业30年以后,我和家人参观梵蒂冈博物馆,站在《拉奥孔》雕像前时,我和家人分享了曾经在大学里读到的知识和感受。大学是阅读的地方,阅读不仅仅给了知识,阅读对人生的影响在于它能够成为人生的一部分。在人生旅途的某个时刻,一些曾经在大学时代零零碎碎的阅读会聚合成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兴奋不已,给阅历累积已经变得程式化的生活添加了新的活力。大学一起了头就没完没了了。毕业30年以后,2014年我回到上外工作,和王老师谈起当年读《拉奥孔》、温克尔曼和市民悲剧的情景,谈到许多细节时,王老师疑惑地说:“我不记得了”。老师可能记不住课堂的细节了,大学对人的影响却正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发效,在无形之中塑造着一个个形象,这就是大学的魅力吧。“粮食风暴”听杨寿国老师上翻译课像是听神奇的故事,正课上教了什么和学到了什么不记能记住,但他在课堂上讲述翻译《阿登纳回忆录》的事,至今记得清楚。据说,那是北京下达的紧急任务,因为回忆录里记述了阿登纳1955年9月在莫斯科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时,赫表示中国人不可信,对苏联是个麻烦,希望德国帮助苏联对付中国。这样的信息自然引起了北京的重视,所以要迅速把此书译成中文,供“内部参考”。那时,有不少书是供内部参阅或批判的。我们这一代人中苏斗争的意识很强,知道了很多苏联欺负中国的事,如1960年关系决裂,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不讲信用。听了杨老师的讲述,我还是觉得吃惊,没想到苏联早在1955年中苏关系还在形式上亲如一家、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信任中国,甚至要让德国帮助它对付中国。有意思的是,这也与当时正在读的霍布斯的“人对人是狼”的断言结合在一起理解。当时的印象是,苏联对中国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于是更觉得苏修的确很坏,也觉得杨老师他们能够承担北京直接下达的任务,很了不起。由此,讲到上外建校初期的学生由老校长姜椿芳带领北上,到马列编译局翻译马恩列斯著作的事迹,其中像《反杜林论》等都有校友参与定稿。这样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到了翻译的重要意义,甚至觉得很神圣。杨老师上课不苟言笑,文字也是极为认真的,告诫同学们翻译时要弄通原文。他举例说,有一本德国小说Sturm auf Essen,中文版书名被翻译成了“粮食风暴”,译者把城市名Essen望文生义地译成粮食(das Essen)了。小说描绘的是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埃森市为中心鲁尔地区矿工闹革命的故事,开头是到前线当兵打仗的工人们战后回到家乡,家人惊喜高兴,孩子们期盼着父亲带回了“神圣的面包”。这的确和粮食有关,但不能因此翻译成“粮食风暴”!故事主要发生在埃森市,这里有克虏伯等“反动派”的强霸,是工人闹革命的对象,故事的结尾大意是革命没有成功,大众还更在乎“粮食”,吃饱肚子更重要。在杨老师的翻译课上,我们在文本和故事中实际和具体地接触了苏联、一战后的德国、西德、东德的生动侧面。也许,他可能是随意讲了些与课程相关的故事,但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师的讲述激起好奇和探索,这正是学生成长的道路。这应该就是老师“功夫在课外”的道理吧。翻译课是语言课,但又不仅仅是语言课,它让我们进入了语言所表达的生活世界,它离我们很远,但又近在咫尺,感同身受。每个老师的课都像是一块马赛克,在学生的认知和想象中被一个个地拼构起来,形成学生自己的图像。尽管老师提供的材料是一样的,但经过学生的加工,却变成了各色各样的图案,这是神奇的过程,也是大学丰富多彩活力的写照。“偷听课”我还特别想写写大学时偷听过的课,印象深的是:首先是到英语系梯形教室里听过《欧洲文学史》,有机会系统了解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文学,这补上了仅仅在德语系学德国文学的短板,扩展了视野,由此激发出阅读这些国家经典文本的兴趣,把欧洲文明史中的代表人物拉入自己生活的景象之中,相互认识和交流,彼此之间有了关联,也由此对欧洲的精神和人文历程有个入门的了解。这门课程不在学校教学规定内,但给我的大学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可惜不记得老师是谁了。英语系的讲座也很多,诸如英语系同学自己举办和讲述的“西方美术史”等,记忆中的梯形教室一直很热闹。我还到音像中心听一位叫哈桑的美国学者讲文学。不知他是何人,但听说是讲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马上被吸引住了,要听。那天的讲座好像是在录像,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这位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溜进去,乖乖地躲在后面听。印象中,哈桑很和蔼,语言出乎我意料地简明清晰,似乎他说的话都能听懂,其实,单个的词句可能听懂了,放在篇章层面上还是听得稀里糊涂。事实上,听懂多少不再重要了,令自己兴奋的是,我去了,我听了,而且获得几个新的词,哪怕是听错了,也是收获。那时,常拿“创造性误读”为自己的不求甚解做借口。我似乎听到哈桑教授讲到了文学批评中的解构问题,把作品相关的要素拆开来观察分析,是为了再组合起来得到整体的印象。这样去讲述作品分析的方法和途径,让我感到新奇,觉得像语言医生一样对各种句子做外科手术,打开了再缝合修复,这种想象持久保留在脑海中。由此再去翻阅相关的书籍,在德国格式塔心理学那里居然找到了对应。不同的是,后者认为人对事物的感觉是整体感觉,就像我们读书并不全是一字一字地读,而是成行地、甚至“一目十行”地读。再如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不是先去分别感觉其耳鼻喉面,然后形成关于他这个人的整体图像,而是上来就整体“扫描”他,感觉他。现在看,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但那时却为自己“发现”了新的关联、新的境界而兴奋不已。这和学习外语当然有关,那时读到一个用来反对语法教学法的故事:某人欲学会一门外语,得知其基本语法规则和词汇,以为掌握了这些便可会说这门语言,于是就全力以赴很快掌握了那些规则和词汇,但出他意料的是,他并不能讲那门语言。学习外语在于日积月累,直到某个时刻“猛然顿悟”,上一个台阶,突然觉得自己不再跟着语言规则跑、总怕得罪它,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组合语言,让语言跟着自己的意思走。听余匡复教授讲德国文学是很享受和难忘的经历。他给本科生上文学史,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突出重点,讲得风趣,上来就从中世纪骑士诗人(游吟诗人或爱情诗人或恋歌)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讲起:Du bist mein, ich bin dein, dessen sollst du gewiss sein, du bist verschlossen, in meinem Herz, verloren ist das schluesselein, du musst fuer immer darinnen sein. 爱情诗对年轻人当然有吸引力,抑扬顿挫的音调朗朗上口,易记易诵,文学变得很鲜活,岂能不喜欢!文学课,比较怕的是只讲道理,没有作品,应该首先是让学生品读文本,然后再讲文学理论和历史。“罢课”按规定,进入三年级后要学习第二外语,首先大家都要学习英语。出乎意料的是,英语课十分简单,几位同学不得不和老师“交涉”,但老师没有办法修改,原因是教学计划规定好了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不可随意更改。交涉没有结果,只好“罢课”,然后去参加了一个考试,争取到英语免修。三外改学了法语,这是自愿的,学不学由自己定,因课程安排冲突实际上就不了了之了。大学里没有学好法语,是很遗憾的事。自己不重视是主要原因,但学校在排课方面没有提供时间条件也是客观原因。给学生提供学习多语种的可能和条件,至今仍是外语类专业的面临的挑战。如何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地组织大学的活动和内容,这个问题至今还没能很有效地解决。工作:参与外语教育规划198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高教一司工作,在外语处工作了六年。现今回头看,那一段和外语教育的缘份让我很难忘:(1)适逢国家改革开放大业起步,政府最高决策层对外语教育高度重视,比如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范围内的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一是1978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国务院提出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把外语教育抓上去,多快好省地培养各类外语人才;二是1982年的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要求对全国中学外语教育进行全面规划,统筹推进。刚到外语处,常听到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工作也是落实相应的事项。(2)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设有专司外语教育的机构,高教一司外语处系统负责全国高校(本科为主)各类外语教育事业的整体规划、政策指导、标准制订(如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学科专业布局(如新专业点审批)、学术组织(如各语种教材编审组和教学研究会等)、重点措施(如教材编写、师资培训和考试评估等)实施等,是外语教育事业的“司令部”。我到该处工作那段时间里,处长是蒋妙瑞,副处长任丽春、董威利,工作人员有许宝发、曾耀德、倪肖琳和我,主管司领导是付克同志。当时,领导们还在讨论成立外语司的可能性,把外语处主要负责“正规”高校本科外语教育事业的职能扩展到基础教育、继续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阶段等,进一步统合各类外语教育,综合提升外语教育的水平。当时支持的观点认为,外语能力和“计算机的能力”是横跨不同学科、专业和阶段的能力,应该系统规划,整体发展。不过,这一设想不符合此后国家机关精兵简政的大趋势,设立“外语司”的设想未能实现。到90年代,教育部外语处被撤销,外语教育的整体规划和布局的职权逐级下放或由相关领域及行业的职能部门分别负责。(3)外语教育行政与外语院系互动密切。那时,外语教学的重镇如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领导和专家是外语处的常客,经常看到胡孟浩、桂诗春和王福祥三位外语学院的院长,与季羡林、许国璋、李赋宁、刘和民、严宝瑜、杨惠中、祝彦、殷桐生、梁敏等学者的联系十分密切。当时我经常跟着领导骑自行车从北京西单(外语处)到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关村(北大、清华)找学者咨询商议工作,时间晚了就住在北外学者家里,我曾在北外和北大多位学者家里“蹭饭”和过夜。本质上,这样的“工作关系”是管理层与专业界的互动,但那时却没有丝毫的“官民”区别,大家是一个整体,像个大家庭。外语处没有什么“好处”给大家,委托的项目钱很少或根本没有,大家参与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意思”,报酬和名分的意义不像如今这么重要。(4)各类制度和组织在建立中,教育理念方法在变化中,各类教材资料在建设中,各层师资在培训中,各种外语考试(包括四六级和四八级考试等)开始设立,现在看,那是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创制时期,能有机会参与见证其中,很幸运。这里举两个我在外语处工作时的经历,说明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很系统、很具体地管理着外语教育,一个是关于外国语言的,另一个关于外国文学。教育部系统组织外语教育的全过程,包括理念、理论、方法和主要措施,可谓“一竿子扎到底”。1984年8月中我到外语处工作几天后便平生头一次坐飞机到昆明参与组织举办西南片高校教师参加的大学英语研讨会。按当时规定,只有县团级以上人员才有资格坐飞机出差,而我只是个“新兵”,居然可以坐飞机出公差,可见决策者对此次会议的重视。那时才知道,大学英语就是公共英语,之所以改称大学英语是提高了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改变其在大学的从属地位。树立大学英语的概念在当时很难得。那时,大学英语有了自己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整个大学外语(即公共外语)教育理念、模式、方法和支撑奠定了基础。印象中,昆明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两百多名大学英语老师参加,主要听专家们讲解新的大学英语的理论依据、方法、内容,交流各自的经验。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密集地听到关于外语教学法的各个流派的介绍,比如传统的语法教学法、新的听说法、情景教学法和功能交际法等。那是一系列培训活动的一部分,对革新全国的外语教育理念起到了很大作用,促进了外语教学水平提升。新方法提倡使用真实的语言交际材料,大量原版和原文的内容由此进入了教育体系,使学习者在习得外语时,也能直接从文本上接触外部世界,打开视野。从这一意义上讲,外语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直观部分和直接能力建设。那时已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概念,认为这是外语学科的重要内容。现在看,那也是受了英美的影响,超越偏重语法的传统,进入文化和生活领域,使语言直接交际,嵌入英美日常,登入英美制度,在体验和感受英美现实生活中习得语言,培育起亲切的关联。积极意义上说,中国民众学外语,看世界,开拓了眼界,为开放改革奠定了知识和认识基础。当时英美两国驻华使馆和文化教育机构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协助中国推进英语教育,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的也是外语处的常客。他们中的不少人是语言教育专家,甚至是国际应用语言学界的著名专家。80年代末,德国等国家的语言教育机构如歌德学院也进入中国,也都高度重视和外语处的合作,希望“在体制内发挥作用”。中德高校德语助教进修班就是教育部与德国外交部合作的政府项目,系统培训德语教师的教学法能力。现在,高校外语教师系统的教学法培训少了,高校外语教师基本上是干中学,他们的大多数是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任教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学法训练。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系统规划和推动工作很细。1985年秋,我被临时调到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工作小组工作,地点在北京大学勺园,我主要参与的是外国语言文学部分,其中一项工作是跟着 武兆令和严宝瑜教授征询学者意见,包括季羡林、朱光潜、罗大冈、冯至、绿源等,还要直接组织专家 召开咨询会。虽然已过去30多年,但不少内容仍有现实意义。上海地区专家咨询会于1986年3月21日和22日两天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三楼会议室召开,为制订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划出谋划策,国家教委没派人与会,而是调取会议记录,收集专家的意见。会议记录和专家意见由我整理上报处、司领导。会议由上外胡孟浩院长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袁晚禾、龙文佩、林珂、秦小孟、朱雯、余匡复、王长荣、廖鸿钧、朱威烈、倪蕊琴、朱逸森、吴克礼、刘犁、胡孟浩和谭晶华。部分专家发言作为史料摘录如下,以飨读者:朱威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有很多空白要填补,然而这是仅仅停留在翻译方面,研究方面还做得很少。目前我们要编阿拉伯文学史,还需要资料。现在阿拉伯文学再不抓的话,很可能在中国又要出现像“大熊猫”的现象。研究阿拉伯文化,目前肯定要赔钱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赔钱就不搞,还是要搞。现在我们已经派人出去学习,相信若干年后会有起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很重要,精神文明需要抓。谈到开放,不仅仅对第一第二世界开放,对第三世界也要开放,特别是他们的文化。对此,出版发行部门要支持,要支持杂志的发行。这方面国家教委也要支持,要保证学术刊物的发行。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要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挂起钩来。谭晶华:现在学生讲是“没有劲”的文学,这与我们的研究介绍不够有关。根据目前对日本文学研究的情况,“七五”期间要抓紧,过去我们对日本文学的介绍比较杂,以后可以系统地介绍。余匡复:对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很需要,现在学生在这方面很感兴趣。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当代比较文学的开展很重要。另一方面,资料工作也很重要,现在外国这方面就很重视。要搞研究就要有资料。要写评撰就要多看作品和资料。同时在研究中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有突破性的东西。现在外国对中国的文学很重视,搞老庄的有,搞“五四”文学的也有,搞当代的也有。因此我们现在搞比较文学研究很重要。在搞这些工作的时候,教委要在物力、人力上给与支持。另一方面,学术讨论要给予充分自由,领导不要轻易在报上讲话。在文学讨论中,要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要有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气氛,错误的东西让发表出来也可以讨论批评。朱逸森:现在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还很不够。这次从上面来做很需要。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该怎样来做,我认为在评撰方面很重要。就我自己搞的苏俄文学来讲,现在国外研究很多,我们也用自己的人力,财力来进行更好的研究。我们可以抓住一个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工作,以开拓新的研究局面,并在某一点上有突破。文学批评也很需要搞,现在我们的评论工作也搞得不够,原因就是没有新的突破。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也很重要,首先我们要编写出文学史的书,要搞好资料工作。要重视资料工作的收集,没有资料很难开展研究工作。要组织一定的力量。对去国外搞研究工作的人,回来时可以给一些钱带些国外的资料回来。倪蕊琴: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人的东西要有自己的东西。研究外国文学,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这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在探讨新的方法论上,要担风险。我在学校教苏联文学,一讲苏联文学,学生们就要同中国的文学作品相结合来谈。因此,现在讲中国的“伤痕文学”已不讲了,现在只讲“转折时期的文学”。现在中国文学继承外国文学的东西已经比较多,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这就是说现在的比较文学课题很需要。现在科研经费很少,搞比较文学就更少,搞个比较文学课题的研究很不容易。苏联的文化对于我们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对苏联的东西很值得研究。现在西方对我们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是古典东西。对于外国文学史,我们也应该搞,但要细致地搞,这对现在的学生教学很需要。这也需要一定的力量。师资问题,我们也要加紧培养,对于俄语来讲,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俄语好的很少,因此对苏联文学的研究很需要一代青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要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另外,翻译作品,现在很难被重视出版,一本书出来,订数很少,这也希望能采取一些措施。朱雯:“六五”计划的成就还是很好的,几套丛书: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丛书,二是文艺丛书,三是外国文学丛书(略)。教材编写不足,“七五”规划中要加强,编写出质量高的外国文学史。另外,关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评论我们做的也不多,是否规划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研究,写出他们的传记和质量高的评论文章,要在翻译过程中同研究相结合。胡孟浩:文科现在很穷,教委各方面要支持,也可以采取鼓励的办法,出些研究题目,哪个学校愿意承担,就多给一些经费。以后高校文科单位分配资金,我认为上海方面也可以出一个人。这次座谈会的很多意见,诸如外国文学史(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等)被列入规划,受到支持和推动。与现在激烈竞争的热闹场面不同,当年是要“求”专家接受课题研究的,我就到北大西语系和北外求过。驻外:以外语为工作语言1996年我第二次被派到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处工作,任一等秘书外联组长,任期四年,主要工作之一是开展德国教育调研,密切关注德国教育政策动态。那段时间印象很深的是,德国传统大学的汉学系经历着深刻变化,有的缩小了,如波恩大学汉学系;有的索性被取消了,如哥廷根大学汉学系;留下来的也被整合进当时流行的“区域学”“中国学”(Regionalwissenschaften,Chinastudie),整个专业分语言和专业两大部分,语言是基础,为专业学习服务,使学生在语言的基础上获得相关国家的地理、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知识,培养理论、方法和实践能力,也强调就业能力的培养。这与我国大学外语专业语言贯穿始终的做法很不同。在调研中,我曾以汉语为例介绍了德国外语教育的特点,特别强调外语专业应该注意借鉴欧美大学做法,重视传授国别区域知识。2008年我第三次到驻德使馆工作,任公使衔参赞。“外语教育情节”仍然让我格外关注德国的外语教育,与多所德国大学合作,促进或协助其汉语和中国学专业,包括协助他们开设汉语师范课程等,与汉语界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前,哥廷根大学停办汉学系曾让我很沮丧,2009年该校重开中国学,重点放在历史和社会方向,我与校校长von Figura教授、副校长Casper-Hehne教授密切合作,代表汉办提供了大力支持,按协议资助两个教席。汉办领导介绍,这在当时是中方单独对一所外国大学资助力度最大的。第三次在德国工作期间,我还关注了欧洲大学开设中国学和“台湾学”的情况,专题报告建议国家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国外中国学建设,在国内高校推动开设中国学课程,与国外中国学加强学科合作。再回母校:探索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2014年1月7日,我遵教育部调派从德国回到北京,8日到上海,9日被任命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我本科毕业于此,现在又回到这里为母校服务,跟随至今的外语教育情结有机会进入实践。紧张深入的学习和调研之后,我认识到,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作为学科和专业与我30多年前所认识的变化不大,与我比较熟悉的德国大学外语教育和了解到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以及韩国外国语大学办学实际相比,我们重视语言有余,但理论方法能力培养不足,国别区域知识供给不够,需要立足时代变化,着眼国内国际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外语教育的改革发展,其中,学科和专业建设是基础。欧美日韩外语专业结构改革应该是15年前的事了。经过反复研讨,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6年7月正式确定把学校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办学目标,强调要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学校着力探索专业特色型、多语复合型、战略拔尖型三大类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原来的单一化、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以学生为中心,增加学生选择的自由度,提供个性化、自主化的培养方案,优化、充实课程设置,基于“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重新构建学生的知识结构。学校还开设了英文授课的中国学硕士学位课程,启动了多语种、跨学科、跨院系、国际合作的“国别区域特色研究生班”项目,希望以此为创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模式、培养具有新时代全球能力的人才做出上外应有的贡献。我国外语学科如何融合国内外丰富经验,面向未来,针对现实问题,主动回应国家和社会需要,创新学科内外发展还任重道远。对新时代外语教育的思考可以另文撰述了。姜锋,博士,1962年12月生于山东,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第七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曾在教育部高教司、社科司、国际司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来源 |《外国语》编辑 |李磊阅读上外多语种资讯,欢迎访问http://global.shisu.edu.cn© 上海外国语大学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SISUers/ 订阅号:sisu1949
编辑:
(本文转载自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MBAChina立场。采编部邮箱:news@mbachina.com,欢迎交流与合作。
备考交流
最新动态
推荐项目
活动日历
2022年度
- 01月
- 02月
- 03月
- 04月
- 05月
- 06月
- 07月
- 08月
- 0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11/03 上海线下活动 | 港中大MBA课程2025级招生宣讲暨校友分享会
- 11/03 上海站 | 港中大MBA宣讲会暨校友分享会
- 11/03 学长学姐校区见面会 | 香港大学在职MBA(大湾区模式) 十一月线下咨询会报名
- 11/03 下週日見!2025年入學交大安泰MBA第一場港澳台申請者沙龍重磅來襲!
- 11/06 讲座报名 | 房地产市场的破局与重构
- 11/12 统考倒计时45天 | 清华科技创新MBA学姐备考分享&答疑等你来!
- 11/13 线上活动|备考经验高密度输出,招生动态前瞻解析,11月13日交大安泰MBA考情解析+笔试技巧分享会开启报名!
- 11/14 公开课抢位|人工智能、数据和人才@北京
- 11/14 申请冲刺 | 港中大(深圳)MBM2025级第四批次招生启动!
- 11/14 活动日程 | 11月14日港中大(深圳)MBM2025级招生说明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