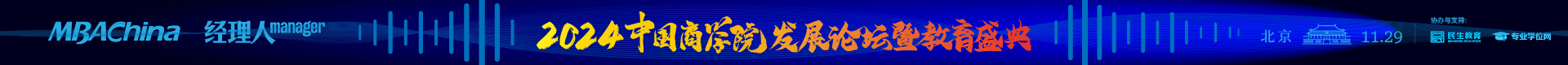黄渝祥:走向世界,走向开放 | 师·道



生于四川的黄渝祥教授,把四川老乡邓小平视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力主恢复高考的同时,还要求派遣一批知识分子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冠名为“访问学者”。这是为改革开放储备人才,当时还是同济大学青年教师的黄渝祥就是受益者之一。
人生的际遇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大学时期一次偶然加修英语课的经历,让黄渝祥成了为数不多符合出国条件的人。从历史维度看,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则是不可逆的时代必然。或许,从1980年踏上波音707客机飞往加拿大的那一刻,“开放”二字就已深深嵌入他的生命轨迹中。
回国后,黄渝祥受聘担任世界银行的咨询专家,将费用效益分析、可行性评价等先进技术和思想引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地方进行项目建设的标准。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黄渝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让他对经济效益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市场规则抱有深切的尊重。在参与南浦大桥、京沪高铁等多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咨询中,这些信念贯穿在他工作的方方面面。
记者在一栋普通的单元楼里,见到了黄渝祥。虽已桃李满天下,甚至不少学生已身居高位,黄教授的生活仍然十分简朴。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那些参与国家建设、拥抱世界的光辉岁月成了他一生珍视的财富。
黄 渝 祥

1940年生。同济大学教授,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技术经济、项目评价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主要论著有《工程经济学》《费用效益分析》《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等。
老教授讲课一点“疙瘩”都没有
记者:当时为什么选择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
黄渝祥:我是1958年考入同济大学的,刚开始报的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报到后,学校把我转到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想学工科,不愿意学经济管理相关的专业,但我没法做选择,就这么转过去了。
现在回顾觉得也蛮好,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的特点是建筑和经济两面兼顾,学制五年,前三年半学习建筑学和力学等课程,后一年半学经济管理,当时的经济管理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
记者:在同济学习期间,专业的办学情况如何?
黄渝祥: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同济大学成为以土木建筑学科为主的学校。当时我们这个大系包括建筑学、规划、建筑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5个专业。我所在的专业由于是新创办的,师资力量相对较弱,而偏重于建筑造型的建筑学专业,师资力量比较强。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是冯纪忠,他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和贝聿铭是同班同学。
记者:还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老师?
黄渝祥:有一位教我们数学的教授叫王福保,当时50多岁,他是同济版《高等数学》的编者之一,全国的大部分工科院校都用这本教材。当时这些编教材的教授,学术能力很强,但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面,一心一意把教材编好,而且要适合工程类学生使用,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还在用这部教材的原因。
现在我到其他高校去看,基本上还是这些内容,几十年没有太大变化,说明这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记者:还记得老师怎么上课吗?
黄渝祥:王福保老师上课从不带书,也不带讲课笔记,就拿一支粉笔,他清楚记得上次讲到哪里,直接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对于重要的问题,他甚至可以讲十来遍,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讲课一点“疙瘩”都没有,非常流畅,推导的板书也非常清楚。
当时教我们的老先生大部分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硕博士,专业能力非常强。我记得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我们理论力学,有一次,他发现我的解法跟他讲的思路不同,他看了好久,觉得我这样答是错的。但他还是按照我的思路演算了一下,发现没错,他谦逊地说这是另一种解法。
交卷后去江湾体育场游泳
记者:您当时成绩怎么样?
黄渝祥:成绩还算不错,高等数学、力学都是很难的课程,老师也都很严格,仅力学就要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这三门,我本身对数理就很感兴趣,基础也比较好,所以学得比较快。
我记得当时教结构力学的是个年轻老师,他给我们出的考题都不算难,结果我第一个做完就交卷了。老师看看周围没人交卷,他当场就批改了,写了个100分。
我想做完了干啥呢,就到江湾体育场去游泳,没想到游完泳回来他们还没考完。前面三年主要就学这些东西,我基础比较好,评三好学生都有我的份。
记者:除了专业课,还学些什么?
黄渝祥:三年级下学期,学校从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加修一门英语课。当时我们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从高中到大学,我学的都是俄语。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很厉害,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邹廼之,当时英语老师很少,他教了我们一年,班上大概有20多个同学,都是来自不同专业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件对我一生都很重要的事。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黄渝祥:对我来说,学英语是一个很大的转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同时要选派一批像我们这样的中青年教师到国外进修,叫作“访问学者”,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学过来,然后才可以教大学生,为改革开放做准备。
因此,1979年同济大学宣布了出国进修计划,选拔的人员需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40岁以下,第二个条件是在“文革”前毕业,符合这两条的已经不多了,我是1963年毕业的,那个时候是39岁,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麻烦了,要考英语,国家出钱派你到国外去,不懂英语怎么行?英语考试实行全国统考,笔试和口试我都过了,跟那个英语班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要知道在上英语班之前,我只在初中学过英语,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后来我发现,通过英语考试的人,大部分都是当年我们这个英语班里的同学。

黄渝祥参与编纂的部分图书教材(顾杰 摄)
毕业后去建筑工地做木工
记者:听说您毕业后曾经去工地劳动,这是怎么回事?
黄渝祥:1963年我毕业后就留在学校当老师。从1964年到1965年,我到工地参加劳动,因为当时教育部有规定,新的老师或者助教一定要参加专业实习劳动,所以我们那一批留校的青年教师就去了工地,当时我是去吴泾的建筑工地做木工活。
记者:您在工地上具体做些什么?
黄渝祥:当时要建吴泾化工厂,锯锯子、钉钉子,甚至搬运木料等体力活我们都得做。不过我才20来岁,这些体力活都能对付得了。
后期就和专业结合了,在我们这些学生去工地之前,设计院的图纸一般的木工是看不懂的,只有退下来的高级木工读得懂。但我们学过建筑制图的课程,所以能读懂图纸成了我们的优势。师傅就让我专门干这活,由我负责把一项项任务分配下去,后来我相当于成了木工队的队长。我在工地干了一年,这一年对我帮助还是挺大的,那是正儿八经在第一线劳动。
记者:您和工地的工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黄渝祥:我们是正经拜师的,真正把工人当老师看待。师傅们人也挺好,手把手教我们,平时吃住都在一起,晚上睡在工地的临时工棚里,还经常跟他们聊天。他们对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很尊重,虽然有些师傅不识字,但人都很聪明,经验也很丰富,大部分都是祖传的手艺活,脑子很灵。
记者:当时和工人师傅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
黄渝祥:有一次,我把某个方案给木工师傅做,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个老师傅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少做了一根梁。刚开始那位老师傅还不服气,我就把图纸拿出来给他看,他看后发现果然是自己错了,于是一句话没说连忙拆了重新做。
我们和师傅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临别时,他们还把自己祖传的全套工具都送给了我,有刨子、锤子、斧头、锯子。后来我用这套工具在家里做了很多木工,有小板凳、椅子、沙发等。
出国在大衣领子写上名字
记者:讲讲您的出国经历吧。
黄渝祥:刚开始我还不当回事,因为觉得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够根红苗正,还有点海外关系,出国应该轮不上我。
后来人事处来通知时,我说你别开玩笑,对方说这怎么能开玩笑,确实派你去。当时同济大学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去,后来因为去的人实在太少,条件放宽了一些,年龄大的也能去了。
记者:出国前需要作哪些准备?
黄渝祥:出国前参加了几次纪律教育方面的培训,那时候我们收入比较低,没有像样的衣服,怎么代表国家出去?于是给每个人800元制装费,当时我一个月工资只有65块,但这个钱不能乱花,只能到规定商店去定做。虽然料子都很好,但每个人的式样都一样,包括衬衫、两套西装,还有很厚的呢子大衣和皮鞋等。
记者:怎么出发的还记得吗?
黄渝祥:1980年2月,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队伍里不只有同济的,全国各地学校的人都有。我们去加拿大的组成一个小队,大概有20多人,有一个年纪比我们稍大的团长,给每个人发1美元在路上用,其实连买瓶水都不够,这些美元都集中归团长保管。
我记得乘坐的飞机是波音707,当时我们只有一条航线到加拿大,得先到卡拉奇,然后转到巴黎,在戴高乐机场待了十几个小时,再飞蒙特利尔。
记者:下飞机后是什么感觉?
黄渝祥:眼前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太不一样了,比我们先进很多。其实当时我们下飞机后还觉得挺自豪的,因为穿的是呢子大衣,没想到我听到旁边几个加拿大小女孩在轻声嘀咕,我记得很清楚,她们说这帮人可能是越南难民。
我们听了当然很生气,后来我们发现自己确实跟加拿大当地人不一样。他们穿的衣服没一件是一样的,我们的式样和料子都一模一样,身高也差不多,自己也搞不清哪件大衣是谁的。为了不拿错,我们在领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记者:您去的是加拿大哪所学校?
黄渝祥:加拿大有很多学校,有人留在蒙特利尔,我一个人去了多伦多大学。当时已经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中国访问学者在那里,他们是之前被派去的。当时出国进修的人里面医生比较多,很多是医学院和大医院的骨干,他们英语比较好,此外还有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理工专业学者。

1980年在多伦多大学工学院
在加拿大研究费用效益分析
记者:在加拿大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黄渝祥:同济教师去多伦多大学的就我一个,当时有点尴尬的是,我出国前在同济是教结构力学的,不是经济管理,所以我在加拿大继续学土木工程还是学经济管理,这是一个问题。当时我也是40岁的人了,如果再学经济管理,起点等于零。
刚开始,我还到多伦多大学的工学院去看了看,发现他们的专业设备还不如同济,显然不是强项,所以最后我选了工程经济方向,主要是费用效益分析。工程经济的好处是既有工程方面的内容,又有经济方面的内容。这个专业当时在国内叫技术经济,实际上研究的对象差不多,也就是研究工程技术的经济方面。工程技术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现在我们的5G、人工智能、导弹等都是技术,无论技术为社会服务还是为国防服务,经济账总要算。
记者:当时选择这个专业,和您的老师有关系吗?
黄渝祥:有关系。我们经济管理的老前辈叫翟立林,他就是研究工程经济的,也是同济大学管理工程学科的奠基人。出国前他就劝我还是要回到经济管理领域来,因为我们国家需要,尽管这专业没有很深的学术内涵,但是比较实用。我也觉得,工程经济对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是马上就能用的。
记者:当时研究学习的内容中,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
黄渝祥:费用效益分析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是关于公共项目或者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分析。和一般的投资回报不一样,公共项目是要考虑社会经济效益的。比如我们修高铁、水利、博物馆、医院、学校等,不能都按照商业模式来建,因为有些项目没办法量化为钱,而且私人老板也不愿意投资,所以要用另外一种公共支出的模型来分析,这就是费用效益分析。
记者:可以举例谈谈吗?
黄渝祥:当时多伦多大学正在研究纸张的重复再利用问题,其实加拿大的木材很多,纸张不成问题,但他们说不行,要节省木材,教授带头去垃圾桶里把废纸拿出来继续用,这对我触动很大。
到中南海起草重要文件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黄渝祥:1982年,我按照国家规定回国,当时我已经结婚,妻子孩子都在上海。我想,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出去学习了两年,应该赶快回国干活,为国家发展做贡献,所以我一天也没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这批人就被学校当成宝贝,整个国家都把我们当宝贝。
记者:您当时做了哪些事?
黄渝祥:从1982年到1986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对外开放。世界银行、联合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大量的贷款项目都过来了,按照规定,这些项目都要进行经济评价,也就是要做可行性研究。其实投资一个项目,甚至制定一个政策,都要做一个决策前的研究,概括地说就是这个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在经济上是否合理,我当时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当时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吗?
黄渝祥:当时从国家一直到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对这套东西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往往是立项设计结束后就施工,甚至有些决策是“拍脑袋”的。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很欢迎很支持的,因为他们资本多、劳动力少,而我们劳动力多、资本少,投资者很愿意到中国来,所以国内要有人来帮着做这些沟通的事。
记者:做这些工作有什么要求?
黄渝祥:首先英语要过关,当时世界银行来了很多专家教授,但很多项目专业上的名字和术语,一般外语学院的老师翻译不了,所以我在回国后被派去接待专家,同时还做了很多翻译方面的工作。
1985年左右,我一边做翻译,一边做可行性研究,当时有个单位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点就在中南海,他们把我找去,参与起草制定了第一版《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方法与参数》,并以国家计委文件的名义发布。这是一份指导性文件,从上到下建设项目都要参照这份文件。

参加《方法与参数》研究的部分人员,约1987年摄于北京上园饭店(前排左一为黄渝祥)
两座大桥的决策幕后
记者:您曾参与南浦大桥的项目决策咨询,这个项目有何背景?
黄渝祥:当时上海很多人住在浦东,需要坐轮渡跨过黄浦江到浦西上班,也有人从浦西到浦东上班。但当时浦东还没开发,人们的交通工具仍然以自行车和轮渡为主。鉴于这种情况,上海决定在市区建造黄浦江通道,选址就在南码头的位置。
记者: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黄渝祥:当时可行性研究已经得到推广,按照规定,项目建设一定要请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评估,请专家出具评审意见后再报到国家计委审批,这个流程是不能少的。市里面请我做项目经济组的组长,还请了桥梁方面的专家,我们主要是开会并审查相关的报告,具体的设计则由设计院负责。
记者:您还参与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决策咨询,能否谈谈这个过程?
黄渝祥:对于远洋航运来说,大吨位的船只更显示其经济性,但当时上海长江口的航道只能通过两万吨的船。按理说长江是一个很好的航道,但长江口有“拦门沙”,这个地方水深只有7米多,两万吨载重的货船要潮涨的时候才能开进来。
因此要想办法开出航道来,所以就有了长江口航道疏浚工程,但这项工程很艰巨,动用了很多工程院院士做了很大的实验室模型,但由于台风和水流的变化,航道整治后并不稳定。
当时,从港口和自然条件来说,宁波比上海优越,但经济基础不如上海。上世纪90年代末,宁波提出筹建杭州湾大桥,延伸宁波港的腹地,以港兴市。我负责承担经济分析的部分,我当时带的几位学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记者:当时提出的方案是怎样的?
黄渝祥:杭州湾很宽,大部分是浅湾,航道要求不高,所以投资不太大。原先南北两岸交通要绕行杭州,建桥后上海到宁波的行驶距离可以缩短100多公里,节约的行驶费、过路费和时间很可观,即使收较高的过桥费还是有很高的交通量,效益是很好的。原来的方案是桥北岸接上海的金山卫,桥长一些,但绕行距离更短,后来,桥北段移到嘉兴的平湖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1985年和翟立林先生考察扬州港口
汶川地震后赴都江堰考察
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您曾去都江堰考察,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黄渝祥:当时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有些当地的规划主要是同济大学来做,那时上海援建都江堰的一位领导是我曾经的学生,因为他知道我是搞工程经济的,所以他和同济大学联系,希望把我请过去。虽然我2005年已经退休了,但其实还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
记者:到达都江堰后看到怎样一个场面?
黄渝祥:我们是5月20号出发的,一起去的有上海市的有关领导,还有一些研究规划重建和土木工程的教授,以及上海市的对口单位负责人,大概有20人左右。
都江堰的情况其实还好,我是研究工程经济的,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工程就是都江堰。虽然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但是花很小的代价实现了很大的效益。我到当地一看,发现这个工程几乎没损坏,还在发挥着作用。
记者:您提出了什么建议吗?
黄渝祥:都江堰的领导召集我们开座谈会,我只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应该尽可能保留古老的工程设施,不要统统拆除。既然还能用就应该保留,现在哪个工程能够维持几千年呢?只要稍微维修更新一下,就能保留原始的操作办法,为后代留住古代的文明。其实,这也符合工程经济的原理。
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
记者:您曾参与同济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渝祥:早在1987年,我们就开始与欧洲学校交流学生,最早的交流生来自位于德国的商学院,是一个很小的私立学校,就在莱茵河边上。他们的院长来中国访问时与我们谈好,可以考虑学生交流,互免学费,他们还可以为中国学生提供食宿。
学院就让我负责此事,我就一个人去了德国那所学校。那天正值假日,一个学生把学校的大门钥匙交给我就走了,当晚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第二天,我和学校讨论了交流名额等事项,这件事就算定了。

2019年为留学生讲课
记者:交流还顺利吗?
黄渝祥:私立学校办事比较快,大约在1987到1988年交流了两批,每批7-8人,对方来的是学生,我们派出的是年轻教师。他们的学生英语水平很高,对工商管理的知识已达到相当水准,而我们在这方面相对较弱,安排他们的学习可费劲了。
我给他们讲了中国的项目经济评价和影子价格,翟立林先生用德语教他们中国文化,例如“床前明月光”之类的。我还请一些官员为他们介绍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经济政策,我做翻译。德国学生觉得很解渴,提了很多问题,对我来说收获也不少。
记者:您觉得国际交流给学生带来了什么?
黄渝祥:这对学生来说当然有很多好处,我觉得了解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自己又是怎么做的,能够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至少能开阔眼界,没什么坏处。我一直主张要走向世界,走向开放,要多接触,这不仅有利于丰富自己的知识,也能够学习很多国外的长处。
作者:顾杰
来源:《上观新闻》2021-12-03
师·道TONGJI SEM
更多阅读


(本文转载自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MBAChina立场。采编部邮箱:news@mbachina.com,欢迎交流与合作。
备考交流
最新动态
推荐项目
活动日历
- 01月
- 02月
- 03月
- 04月
- 05月
- 06月
- 07月
- 08月
- 0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11/03 上海线下活动 | 港中大MBA课程2025级招生宣讲暨校友分享会
- 11/03 上海站 | 港中大MBA宣讲会暨校友分享会
- 11/03 学长学姐校区见面会 | 香港大学在职MBA(大湾区模式) 十一月线下咨询会报名
- 11/03 下週日見!2025年入學交大安泰MBA第一場港澳台申請者沙龍重磅來襲!
- 11/06 讲座报名 | 房地产市场的破局与重构
- 11/12 统考倒计时45天 | 清华科技创新MBA学姐备考分享&答疑等你来!
- 11/13 线上活动|备考经验高密度输出,招生动态前瞻解析,11月13日交大安泰MBA考情解析+笔试技巧分享会开启报名!
- 11/14 公开课抢位|人工智能、数据和人才@北京
- 11/14 申请冲刺 | 港中大(深圳)MBM2025级第四批次招生启动!
- 11/14 活动日程 | 11月14日港中大(深圳)MBM2025级招生说明会